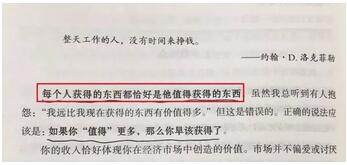《財富自由之路》的作者博多·費舍爾,在書中引用了美國“石油大王”洛克菲勒的一句話:
“整天工作的人,沒有時間來掙錢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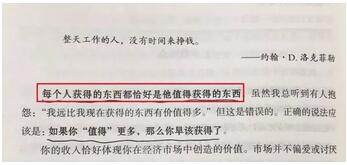
除此之外,費舍爾還在書中補充道:
每個人獲得的東西恰好是他值得獲得的東西。雖然我總聽到有人抱怨:“我遠比我現在獲得的東西有價值得多。”但這是錯誤的。正確的說法應該是:如果你“值得”更多,那麼你早該獲得了。
之所以這麼說,並非是費舍爾危言聳聽。反之,他還留下了一條非常客觀的經濟原理:一個人的收入恰好體現他在經濟市場中創造的價值。
市場並不偏愛或討厭你,它只會根據你的價值來付酬勞。換句話說,雖然我們不能用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,但市場是無情的、客觀的,它起碼能反映一個人所具備的經濟價值。
這個道理十分淺顯,以至於大多數人都不願意承認。所以,這句話最冷酷之處,便在於它時刻提醒著我們:忙碌工作之餘,也要多去反思每個人與財富之間的關係與價值邏輯。
比如,對真正的有錢人來說,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所謂“什麼方法才能賺錢”的問題,而只有,“要怎樣解決某一個問題”以及“怎樣調動自己能調動的一切資源”這兩個問題。
看錢不是錢而是工具,就是一種能力。
許多人商海沉浮數十年,即便傾家蕩產依然還能東山再起,靠的也不是具體的門路,而是比一般人高出一個層次的思維和意識。
就像《1942》裏的地主在流亡路上和長工說的,“我知道怎麼從一個窮人變成財主,給我十年,你大爺我還是東家”。
想在中國賺大錢,有一些基本的規律和共通的觀念,按照重要性排列大致有:
紅利思維
從70年代末開始到80年代初,搞投機的個體戶是第一批發財者,而這些人往往是被主流國營經濟拒之門外,被逼無奈才出去闖的。
到了80年代中後期,發財的人又從體制外回到體制內。依託村或者集體社,利用自身在原有社體制內的聲望或者職務(村長,支部書記),集資辦起了加工廠的人成為第二批暴富者,這一波機會和體制轉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,以蘇南模式(華西村)最為典型。

90年代早期的價格雙軌制改革和90年代後期的國退民進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利用國有資本變賣的機遇,抓住了廉價買賣產權的機會。
2000年開始到2005年。加入世貿又給出口加工業帶來歷史性的機遇,貨代、紡織品出口都養肥了大把沒有文化的沿海小老闆。
2005年的時候隨便開個什麼礦,之後的商品大牛市會讓你的錢多到用麻袋裝。
至於商品房改革、股權分置改革、資本市場的發展更是和每個家庭的財富息息相關。以前老有人說看新聞聯播致富這個梗,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大的暴富機會,中國在過去20年出現了不下十次,最大的機遇幾乎全都和政治格局變化息息相關。其基本特點是一波流。
一波三五年讓你賺個飽,但這波賺完還想繼續賺,幾乎不可能。煤礦、進出口加工,這才幾年而已,現在已經在生存線上掙紮。
稀缺思維
在中國,要預測社會未來的走向,一個最簡單、最基本的思路就是“中國在走美國的老路”。這也就是所謂的CTC(“Copy to China”)的基礎。可以說是中國最近20年所有新興行業的一條發展主線。
這條主線之清晰、之連貫,和前面所說的靠政治趨勢賺錢的一波流的短暫易逝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從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的中國第一次互聯網泡沫開始,一直到前些年的第二次互聯網泡沫,幾乎所有成功的,體量在百億美元以上的新興企業,其產品最初的雛形,都是一個“中國版的美國XX”。

解決稀缺是一切生意的根本宗旨。賺錢這回事,其根本意義,是“為他人解決問題”,而所謂利潤,無非是為他人(社會)解決某一問題的酬勞。
而從無到有,從0到1的事情,從滿足稀缺性需求的角度,要遠比從1到10的事情值得去做。
從經濟學角度來講,最緊缺的東西才是最有價值的,故而得到的回報也不可同日而語。
BAT這些搬運工起家的巨頭,解決的都是從無到有的局面,之後那些跟風的早已在格局上輸了,只能吃幾口殘羹冷炙而已。
ROE思維
如果從財務上來解釋這一點,那就是ROE(股本回報率)=利潤率*周轉率*財務杠杆比率。
注意這三者是乘數關係,所以利潤為負的情況下,失敗也會被這個放大器給放大。
但即便如此,所有賺了大錢的人,幾乎沒有不用到杠杆的,敢下注本來就是企業家精神的一部分。
窮人是手裏有多少資源才敢做大事情,富人是先想到要做多大事才開始考慮要如何籌措資源。熟練運用財務杠杆的前提,就是敢於去動“本不屬於自己”的資源的意識,或者說的再直白一些,敢去借別人手裏的資源來為我所用。

巴菲特扣除杠杆的收益率不過13%左右。被自己有限的資源所限制,說明自己無法掌控資源的流向,依然只是資源的奴隸。
再談一下周轉率。即使是低利潤,只要有高周轉率一樣可以在短期內獲得發展。比如很多人排隊的綠茶和外婆家,菜價便宜但翻臺率高。當利潤很微薄的時候,提高周轉率依然可以提升ROE。
賣珠寶和賣烤串哪個賺錢呢?很難定論。珠寶的單品利潤算下來可能比較高,但周轉率太低。反之,烤串利潤率低但周轉率要大大增高。
假設同樣的資金投入賣珠寶和賣烤串,並且假設珠寶3個月一個資金回籠的週期(從生產到物流到銷售),烤串一天一個週期(從生產到銷售),那麼在假設兩者都可以銷售出去的情況下,也許賣烤串比賣珠寶更賺。
此外,中間型行業和智力型行業通常有望達到更高的ROE,主要是因為資產較輕的關係。
瞭解自己
研究自己比研究他人,研究金錢更重要。
我們最大的問題,就是對自己的瞭解遠遠沒有自己以為的多。
能賺錢不代表自己就能從錢中獲得享受,對金錢的態度其實是一件特別個人化的事情。大部分人也許可以做到正確衡量各種資源的時間價值、卻往往對自己的時間成本毫不在意,對自己的收益偏好毫無概念。
這種能力需要建立在深刻瞭解自己的身體和心理的基礎之上;同樣的資金、時間,由於掌握資訊的差異,對自己來說,用在哪里最值得,用在哪里對當下、對未來的效用最大,都是需要反復摸索和實踐的。
窮人往往把“錢”看的太“值錢”,把“錢”以外的資源,例如自己的時間,看得太不值錢。
很多人喜歡把賺錢、理財、投資混為一談,其實這是三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,所需要點亮的技能樹也不盡相同。會賺錢的人不一定會理財;會理財和會投資也是完全兩碼事,會投資的人你若讓他憑自己做生意,很可能虧的一塌糊塗。
自己到底最適合做哪一樣,也需要摸索。
很多人對創業有著各種不切實際的幻想,明明是個不夠自律、厭惡繁瑣的人,非要去做生產型企業,殊不知這可以算是最繁瑣的一種商業模式,從原料供應,採購,生產,庫存,物流,銷售,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,毛利潤率又低,必須鑽到每一個細節中去扣成本,可以說一步走錯滿盤皆屬。
對自己不了解,花下去的人生成本是無法挽回的。
防騙意識
這裏的“騙子”是廣義的,泛指一切出於零和動機打你主意的、想從你這裏榨取資源的人。防騙意識的培養,應該貫穿在人生的始終。
投資本身,首先一定是一件反常識的事情,不然有錢人不會在人口比例中占少數。
對於投資,其零和性要比賺錢大得多,所以有時候不止要看到趨勢,還要評估周圍其他人是否也看到了這個趨勢,更要
考慮到周圍人是否知道自己知道對方知道。
如果說賺錢還是人和外物之間的事,那投資就一定是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遊戲。
更加複雜詭異,不僅要防馬路上的騙子、短信裏的騙子,更要防資本市場的騙子,偽裝成“創業家”的騙子、偽裝成“好企業”的騙子、偽裝成“合夥人”、“好朋友”的騙子、偽裝成“情人”、“伴侶”的騙子、甚至是偽裝成“養老金”、“社會福利保障”的騙子。

怎麼閱讀財務報告,怎樣判斷資訊的真實性,知道怎麼查一個生意夥伴的誠信水準;這些東西之重要,可以說分分鐘能讓你半生心血付之東流。
但可惜這些東西對於普通人家的孩子,極少有地方系統的學習,只能靠自己一筆一筆“學費”去交。可又不能因為怕被騙,就因噎廢食,那樣會失去很多機會,不投資必敗,通脹會吞噬你的財富。
過去我們小時候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和家庭教育,對於以上怎樣和錢打交道的知識可謂一片空白。
大部分中國的家長和老師自己也不懂這些東西。既然自己一輩子也沒活明白,那就更不用說教會下一代了。這樣導致的社會差距只會進一步擴大。

總的來說,隨著年齡的增長,很多人對於金錢的觀念越發沉重。所謂“談錢色變”。我們害怕談錢,是因為擔心錢會成為衡量我們價值的唯一標準。
然而,事後看來,這是一種完全沒有必要的擔憂。
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,金錢亦不過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一種產品、一種工具,更重要的是,它背後同樣運行著某種隱藏的同一性規律。
金錢給我們最大的啟示,並不是每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大小,而是它能讓我們看清這個人為市場背後的價值運行規律,讓我們能夠更合理的正視它、運用它、反思它,最終用更正確的方法實現自我價值。
正如赫爾曼·黑塞所說:“我們真正恐懼的不是金錢本身,而是人們對於金錢的欲望。”